requestId:68a75745195cd7.85451783.
一九三〇、四〇年月周作人對儒家的論述
作者:林分份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
時間:甲午年臘月初八
西歷2015年1月27日
內容撮要:本文從辨析一九三○、四○年月周作人對儒家思惟的相關言說進手,探討其儒家論述的獨特徵與復雜性。周氏以“愛智者”的姿態言說儒家“道理”、“中庸”和“事功”,不僅與其思惟構成有關,並且與其自我更換新的資料及自我辯解有關;此外,周氏的儒家論述融會了古希臘、現代科學以及道家、釋家等古今中外多種思惟資源,與“五四”以來各種批評儒家的激進思惟和文明守舊思潮多所分歧;周氏帶有“尋求差別”意義的儒家論述,為其在文明場域中爭取到更多象征性資本的同時,也呈現了動亂時代知識者思惟言說的復雜性。
五四新文明運動期間,周作人與魯迅、陳獨秀等新文明人一路,劇烈批評儒家的綱常倫理和舊禮教思惟。而從五四漲潮后到一九四○年月,周作人也與胡適、陳獨秀等,幾回1對1教學再三對儒家思惟進行感性的再評價。在此期間,周氏曾指出:“我本身承認是屬于儒家思惟的,不過這儒家的名稱是我所自定,內容的解說生怕也與普通的意見很舞蹈場地有些分歧的處所。”①那么,周氏所自定的是怎樣的一種儒家?其解說的內容與普通的意見究竟有何差別?這些差別與周氏本身思惟的發展又具有怎樣的內在關聯?本文擬從一九三○、四○年月周作人對儒家的論述進手,考核周氏對儒家相關思惟的選擇及其與本身思惟發展的關系,從一個側面探勘動亂時代的知識者思惟言說的復雜性。
一
周作人聚會場地之言及儒家,往往從本身對儒家典籍的接收談起。好比對于《論語》,周氏說:“其最得受用的乃是孔子教誨子路的話,便是知之為知之這一章。”②在他看來,“知之為知之”一章所體現的孔子“重知”的態度是中國最好的思惟③,而他也屢屢以此作為本身尋求的境界。因此,在五四漲潮后,周氏宣稱:“現在獨一的欲看是想多求一點知,盡我的微力想多讀一點書,多用一點思考,別的事且不要管。”④為此,他尤其推重希臘古哲尋求學問的精力,指出:“‘哲舞蹈教室學’(Philosophy)本來是從希臘文的philosophia演變出來的,本是‘愛智’的意義。philos是‘愛好’,sophia是‘聰明’的意義。”⑤到了1934年,周氏更認為:“本身覺得文士早已歇業了,現在如要分類,找一個冠冕的名稱,仿佛可以稱作愛智者,此只是說對于六合萬物另有些興趣,想要了解他的一點情況罷了。”⑥而在1937年“七七事變”之前,周氏又說:“希臘古哲有言曰,要了解你本身。我們常人雖于愛智之道無能為役,但既幸得生而為人,于此一事總不成不勉耳。”⑦不難看出,在周氏這里,孔子“重知”的態度與希臘古哲的“愛智之道”其實是一回事。
但是,彼時周作人所謂“重知”或“愛智之道”,其所指涉的內容,重要是儒家基于“道理”(“情面物理”或“物理情面”)之上的認識與評判之道,而非治國平全國的“教條”、“政治哲學”或許“圣學”及其“時文”。誠如周氏指出:“我覺得中國有頂好的工作,即是講道理,其極壞的處所即是不講道理。隨處是物理情面,只需人往細心考核,能知者即可漸進為賢人,不知者終為哲人,惡人。”⑧在他看來,作為三代圣賢思惟的集年夜成者,孔子恰是講“道理”的典范,他不是耶穌而是蘇格拉底之類的人,也與后世禪化的宋儒分歧;而《論語》里邊“有好思惟也是屬于持身接物的,可以供后人的取法,卻不克不及定作天經地義的教條,更沒有什么政治哲學的精義,可以治國平全國”⑨。與此相對應,周氏確定顏習齋在《性理書評》中關于“宋儒是圣學之時文”的評判,認為宋儒“講學諸公只好說體面話,非如三代圣賢一身之出處一言之抑揚皆有定見”⑩。
顯然,在周作人那里,無論“教條”、“政治哲學”或許“圣學”及其“時文”,其所針對的恰是后世孔教徒尤其是宋儒的思惟,而它們都是孔子所講“道理”的對立面。對于儒家的學問和思惟,周氏的品評標準誠如馬時芳《樸麗子》所云:
學不了解,即上文所謂學焉而不得其通,任是圣經賢傳記得爛熟,心性理氣隨口吐出,茍不理解情面物理,實在與一竅欠亨者無異,而又有所籌劃,結果是學問之害甚于劍戟,戴東原所謂以理殺人,真是天昏地暗無處申訴矣。(11)
之所以強調儒者須理解“情面物理”,是因為周氏確信,“理解情面物理的人說出話來,無論概況上是什么陳舊或別緻,其內容是一樣的實在,有如真金不怕火燒,顛撲不破,因為公平所以也就是戰爭”。由此,周氏認為中國思惟界合適此標準的三賢是王充、李贄和俞正燮。三賢之中,李贄雖以思惟得禍,其人看似很劇烈,但“他的思惟卻是頗為戰爭公平的”,因為“他了解真的儒家通達情面物理,所言說一定和藹可掬,不涉于瑣碎迂曲也”(12)。在此標準下,周氏開列的明清以降思惟家實際上還包含了王陽明、袁中郎、鐘伯敬、金圣嘆、傅青主、馮班、蔣子瀟、龔定庵等(13)。
在周作人看來,上述思惟家都屬于聚會場地非“正統派”的儒家。與此相反,“黃梨洲顧亭林孫夏峰王山史都是品學兼優的人,但他們的思惟還是正統派的,總不克不及出程朱陸王的范圍”(14)。實際上,在周氏那里,程朱與陸王也終究有別:“老實說,我是不懂道學的,但不知怎的嫌惡程朱派的道學家,若是遇見講陸王或顏李的,便很有些好感。”(15)有鑒于此,在明清以降的儒家學者中,周氏聲稱最信服的除李贄外,另兩位是郝懿行與焦循。尤其對于焦循,周氏以為,“焦舞蹈教室君的學問淵博當然是很主要的緣由,可是見識通達尤為難得,有了學問而又清楚物理情面,這才幹有獨自的正當的見解”(16)。說白了,周氏之重視非“正統派”的儒家,恰是他們基于“道理”之上的“見識通達”和“獨自的正當的見解”。
所謂非“正統派”的儒家,亦即彼時周作人幾回再三確定的“古來的儒家”或“粹然儒者”。1940年,在《漢文學的傳統》一文中,周氏辨別了孔孟等“古來的儒家”思惟與后世孔教徒的分歧:“漢文學里一切的中國思惟是一種常識的,實際的,姑稱之曰人生主義,這實即古來的儒家思惟”;而“后世的孔教徒一面減輕法家的成分,講名教則專為強者保證權利,一面又接收釋教的影響,談感性則走進玄學里往,兩者合起來成為儒家陵夷的緣因”。周氏這里所謂“后世的孔教徒”,指的是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儒和以程朱為代表的宋儒。與此同時,為了說明“古來的儒家”與非“正統派”的儒家相通,周氏援用了焦循《易余龠錄》卷十二中的一段文字:
先正人嘗曰,人生不過飲食男女,非飲食無以生,非男女無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色好貨之說盡之矣。不小樹屋用屏往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成忘人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學《易》三十年,乃知祖先此言圣人不易。
周氏據此以為,焦循關于“孟子好色好貨之說”的議論,“此真是粹然儒者之言,意思至淺近,卻亦所以就極深遠,是我所謂常識,故亦即真諦也”。因此,自是與“古來的儒家”同脈,而與后來程朱等正統派的儒家異途。在進一個步驟引劉繼莊《廣陽雜記》卷二以及《淮南子·泰族訓》中確定通俗人“愛好”的相關文獻后,周氏指出:“由是可知先賢制禮定法滿是為人,家教不單推己及人,還體貼人家的意思。故能通達情面物理,恕並且忠,此其所以為一貫之道歟。”(17)
周作人對儒家禮法與忠恕之道的闡釋,可謂淵源有自。周氏曾兩次徵引乃師章太炎《菿漢微言》中的統一句話:“仲尼以一貫之道為學,貫之者何,只忠恕耳。諸言絜矩之道,言推己及人者,于恕則已盡矣”。在《漢文學的傳統》中,周氏對此解讀云:“用現在的話說,恕是用主觀,忠是用客觀的,忠恕兩舉則人己皆盡,誠可稱之曰圣,為儒家之幻想矣。”(18)就儒家思惟而言,禮的來源便是不忍人之心,也即“仁心”,其實質與孔子所倡推己及人的“恕道”正相通(19)。章太炎對孔子一貫之道的論述,其關鍵正在于“舞蹈教室仁心”與“恕道”的互通關系,而周氏的闡釋也顯然捉住了這一焦點。因此,在《中國的思惟問題》中,周氏繼續指出:“儒家的最基礎思惟是仁,分別之為忠恕,而仍一以貫之,如人性主義的名稱有誤解,此或可稱為人之道也。”在此意義上,周氏認為,焦理堂的“飲食男女”論,與《禮記·禮運》中“飲食男女,人之年夜欲存焉,逝世亡貧苦,人之年夜惡存焉”所說本是同樣的事理(20)。
確定通俗人的公道欲看,亦即推重儒家重視“情面物理”的態度,此一思惟與周作人所接收的東方現代科學不無關聯。早在1935年,周氏就指出:“所謂常識乃只是根據現代科學證明的通俗之常識,在初中的幾何科學里原已略備,只須稍稍活用就是了。”(21)稍后更說:“……通俗的常識,亦即所謂情面物理。”(22)即便一九五○年月以后,周氏依然認為:焦理堂“飲食男女”論包括了儒家重視情面物理的思惟精華,“將這個意思進步上往,則屬于最高的品德,即是仁,放低了便屬于生物學之所謂求生意志,這原是人類所同”(23)。不唯這般,周氏在將儒家的“飲食男女”與東方生物學的“求生意志”相溝通后,據此指出先儒與西哲在思惟上的關聯:
科學精力,這本來是希臘文明的產物,不過至近代而始光年夜,實在也便是王仲任所謂疾虛妄的精力,也本是儒家所具有者也。我不知怎的覺得西哲如藹理斯等的思惟實在與李俞諸君還是一鼻孔出著氣的,所分歧的只是后者靠直覺理解了情面物理,前者則從學理通過了來,事實雖是差未幾,但更是確實,蓋聰明從知識上來者其基礎自深固也。
將儒家“情面物理”與東方“科學精力”相提并論后,周氏實際上確定了后者更為“確實”的一面。在此基礎上,周氏重申蔣子瀟、俞理初、袁中郎、李卓吾等人的言論“其可貴處是公道無情,會議室出租奇辟橫肆都只是表面罷了”(24)。所謂“公道無情”,便是合小樹屋于“情面物理”或“物理情面”。
周作人后來指出:“經典之可以作教訓者,因其合于物理情面,便是由生物學通過之人生哲學,故可貴也。”(25)其所強調者,依然是儒家之重“道理”與東方生物學在精力上的相通。或許有鑒于此,自1935年始,周氏連續三年在《人間世》、《宇宙風》個人空間上發表他所愛讀的書目。這些書目中,除了《從文自傳》這本中國書外,其他八本外國書如永井荷風《冬天的蠅》、M. Hirschfeld的Men and Women和B. Dawson的The History of Medicine等(共享會議室26),絕年夜多數都是觸及生物、兩性、醫學史等等關乎物理情面的“經典”。此外,周氏于1937年、1943年兩度向讀者開列合適其選擇標準的清儒筆記,其篇目基礎分歧,重要包含劉繼莊《廣陽雜記》、劉玉書《常談》、郝懿行《曬書堂筆錄》、馬時芳《樸麗子》、李元復《常談叢錄》、王侃《江州筆談》、俞理初《癸巳存稿》等(27)。恰是這些體現“物理情面”的清儒筆記,讓周氏在“七七事變”前后的近十年間,以上百篇計的讀書札記,持續不斷地宣傳非“正統派”儒家的思惟和興趣。
二
五四漲潮后,對儒家進行感性的再評價,是諸多新文明人經常觸及的命題之一。1930年,胡適就指出:“孔子是儒的中興領袖,而不是孔教的創始者。”(28)1937年,陳獨秀則徵引尼采的主張,強調“在現代知識的評定之下”重估孔子的價值(29)。就此而言,周作人一九三○、四○年月對儒家的論述,與胡適、陳獨秀等人在總體思緒上差別不年夜。但是,就實際來看,彼時周氏的儒家言說,因其關涉本身經驗、思惟構成的表述,呈現出獨特且復雜的一面。
回顧所受傳統儒家教導,周作人說起十一歲正式讀書時,接觸到的第一本書是“上中”,即《中庸》的上半本(30)。《中庸》為孔子三世孫孔伋所作,原是《小戴禮記》中的一篇,作為科舉時代儒家教導的進門書籍,曾對中國士人產生深遠的影響。但是,就內容而言,《中庸》重要是對《論語》中庸思惟的闡釋,也是儒家典籍中最富有哲學意味的一篇(31),即便像周氏這樣的人,當他五十多歲再次共享會議室閱讀時,也依然覺得:“《中庸》簡直是玄學”,“不知世間何故如彼保重,殊可驚異。”(32)因此,談到本身與《中庸》的關系,周氏指出:“我常同伴侶們笑說,我本身是一個中庸主義者,雖然我所根據的不是孔子三世孫所做的那一部書。”(33)但他又說:“我從小讀《論語》,現在獲得的結果,除中庸思惟外,乃是一點對于隱者的同情。”(34)周氏強調的是,其所接收的儒家中庸,并非直接來自《中庸》里面玄學般的思惟,而重要由《論語》所記孔子的言行中獲得。在此意義上,周氏將孔子推為儒家中庸的“最高代表”、“集年夜成者”(35),并且指出:“中國人從孔子起,至一半老蒼生止,都有中庸的思惟”;“中國國平易近的思惟是講中庸的,不偏于任何一方面。”(36)
所謂中庸,《禮記·中庸》最為簡明的定義是“執其兩端,用此中于平易近”。依據后人的解釋,中庸的思惟焦點即“執兩用中”:由于有兩,固有中,捉住兩端,中就顯顯露來了;而“用”,就是“庸”,用中,也就是中庸(37)。但是,正如周氏自稱對儒家有本身的定義一樣,其對中庸的言說也頗具個人顏色。在周氏看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其特點平凡稱之曰中庸,實在也可以說就是不徹底,而不徹底卻也不掉為一種人生觀”(38)。而這種人生觀,周氏以為,恰是儒家區別于道、法二家的處世態度。因為,假如從思惟而非宗教派別的角度看,儒家“律己有馀而治人缺乏”的中庸,與道家的“隱逸”或法家的“積極”恰是一個人能夠的三樣態度:“道儒法三家原只是一氣化三清,是一個人的能夠的三樣態度,略有消極積極之分,卻不是絕對對立的門戶,至多在中間的儒家對于擺佈兩家總不克不及那么歧視。”接著,周氏以《論語》及《史記》中的孔子言行為例,闡明儒道法三家的聯系:《論語·為政》中孔子說的“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是儒家的幻想,而“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平易近免而無恥”卻是法家的辦法;《論語·微子》中孔子對接輿等隱者的勸告同病相憐,等于認同志家的隱逸戰略;而《史記·孔子世家》記孔子任魯國年夜司寇時誅殺少正卯,用的恰是法家的手腕(39)。后來,周氏又在別一處所指出:“蓋儒而消極則進于楊,即道家者流,積極便成為法家,實乃墨之徒,只是宗教氣較少,遂不見什么佛菩薩行耳。”(40)
對儒道法三家獨特的闡釋方法,與周作人本身思惟資源的構成不無關聯。1936年10月,周氏寫道:“我的品德觀生怕還當說是儒家的,但擺佈的道與法兩家也都摻合在內,裡面又加了些現代科學常識,如生物學人類學以及性的心思,而這末一點在我較為主要。”(41)就實際而言,源于中國外鄉的儒道法三家,與五四漲潮后周氏趨于傳統士年夜夫的心態關系最為直接;而生物學、人類學及性的心思學則源于東方,卻是周氏新文明思惟構成中不成或缺的部門,必定水平上決定著周氏對儒家中庸等傳統思惟的接收。1937年6月,周氏承認,其“談思惟,系根據生物學文明學人類學品德史性的心思等的知識,考核儒釋道法各家的意思,參酌而定,以道理并合為上”。由此他認為“道儒法三家,只是愛智者之分別”,“儒家是站在這中間的”,“我的幻想只是中庸”(42)等等。不難看出,東方現代科學儼然成為周氏評判儒釋道法各家的重要標準,而主張中庸的儒家恰是周氏心目中的“愛智者”一派。
周作人屢次承認,對他影響最年夜的東方現代思惟家,是英國的性心思學家藹理斯(Havelock Ellis)(43)。在周氏看來,藹理斯基于性心思學的生涯之藝術觀,正合于儒家的中庸精力:“其實這生涯的藝術在有禮節重中庸的中國本來不是什么別緻的事物,如《中庸》的起頭說,‘天命之謂性,任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照我的解說便是很清楚的這種主張。”周氏如是說,并且以此反觀中國,認為“宋以來的道學家的禁欲主義總是無用的了,因為這只足以助成縱欲而不克不及收調節之功。”(44)與此同時,周氏屢次援用藹理斯《性的心思研討》第六卷末尾中的兩節文字,此中一節寫道:
有些人將以我的意見為太守舊,有些人以為太過火。世上總常有人很熱心的想攀住過往。也常有人熱心的想攫得他們所想像的未來。可是明智的人,站在二者之間,能同情于他們,卻了解我們是永遠在于過渡時代。在無論何時,現在只是一個交點,為過往與未來相通之處,我們對于二者都不克不及有什么爭向。
所謂“太守舊”、“太過火”的人小樹屋,以及二者之間“明智的人”,庶幾對應于周氏所論列的傳統道、法、儒三家。而周氏尤其指出:“站在二者之間”,“這不僅是一種很好的人生觀,可視為藹理斯的代表思惟”(45)。這種人生觀,亦即周氏所謂“中庸之道”的中庸態度。不唯這般,在強調“明智的人”、“二者之間”等中庸原因的同時,周氏更由此批評那些天天看著日出于東而沒于西,卻總希冀今天是北極的一個長晝的“教徒般的熱誠”(46)。于小樹屋此,借助于藹理斯的論述,周氏將附著于儒家“禮”和“仁”的品德倫理體系之下的中庸,引申為個人在生涯心態與姿態方面“中庸之道”的處世態度,并進而作為批評其他“正統派”孔教徒的思惟資源。
與藹理斯的生涯之藝術觀相類,古希臘人不受拘束與節制的思惟,也與周作人對儒家中庸的闡釋不無關聯。1944年7月,周氏宣稱:“藹理斯的思惟我說他是中庸,這并非無稽,大略可以說得過往,因為西洋也本有中庸思惟,即在希臘,不過中庸稱為有節,原意云健康心,背面為過度,原意云狂恣。”(4)所謂西洋的“中庸思惟”,便是周氏在另一個場合所說現代希臘人的“中庸之德”。在介紹馬池芳《樸麗子》的文章中,周氏寫道:
“夫年夜饑必過食”以下一節實是極年夜見識,所主張的不過庸言庸行,卻重視在能實現,這與喜歡講極端之曲儒者流年夜年夜的分歧。至于說格言至教決不苦物,尤有精義,準此可知凡中國所傳橫霸的教條,如天王圣明臣罪當誅,父哨子亡不得不亡,餓逝世事小掉節事年夜等,都難免為邊見,只要喜偏傲而言行不求實踐的人,聽了才覺得愉快過癮,卻往中庸已遠,深為不佞所厭聞者也。
周氏由此認為:“現代希臘人愛崇中庸之德(sophrosyne),其相反之惡則曰過(hybris),中時常存,過則將革,無論神某人均受此律的管制,這與中國的意思很有點相像。”(48)必須指出的是,正如周氏確定馬池芳的見識“重視在能實現”一樣,其以同樣的目光對待古希臘的“中庸之德”,無形中賦予了后者必定的實踐(用)顏色;而周氏借“中庸之德”將古希臘文明的不受拘束與節制引進來,也確實不乏“考慮到它能夠嫁接到中國固有的中庸思惟的枝上”(49)的實用性動機。但是,二者的實質性差別或許正在于,古希臘有關“中庸之德”(“不受拘束”、“節制”)的辯證觀念,重要來自語言的辯論或思維的規律,而儒家有關中庸(“度”、“過猶不及”等)的辯證觀念,則是來源于實踐(用)感性——正所謂“庸,用也,‘中庸’者,實用感性也”(50)。
此外,盡管儒家中庸來源于實踐(用)感性,但在孔子那里,它是一種難以實現的“道”或許難以達到的境界:“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平易近鮮久矣。”(《論語·雍也》)“全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成能也。”(《中庸》第三章)但是,在對儒家思惟的言說中,周作人借助東方現代科學的感性燭照,不僅將中庸視為中國國平易近思惟和處世態度的焦點,並且將其轉化為權衡個人言行與實踐的品德倫理標尺。1940年,在一篇弔唁蔡元培的文字中,周氏指出:思惟上取“兼容并包”、“并非是過火一流”的蔡氏,乃“真正之儒家”,而“其與後人分歧者,只是收留晚世的西歐學問,使儒家本有的常識更益增強,持此以判斷事物,以公道為止,故即可目為唯理主義也”(51)。周氏所謂“晚世的西歐學問”,指的恰是“生物學文明學人類學品德史性的心思等的知識”;而所謂“唯理主義”,也恰是與儒家不偏不倚相通的古希臘愚人的“愛智之道”。就實際來看,對于曾將儒家不偏不倚與孫中山三平易近主義相提并論且主張師法孔子“智、仁、勇”精力的蔡元培(52),周氏所給予的“蓋棺定論”倒也并非無據。只不過,其中所謂體現蔡氏“真正儒家”的那些特征,與彼時周氏對于本身思惟構成的描寫可謂若合符節。而這,某種意義上正可視為周氏的夫子自道。
三
一九四○年月,談及本身時常置身文壇之外的姿態時,周作人寫道:“雖然我本身標榜是儒家,實在這種態度乃是道家的,不過不克不及徹底的退讓,還是難免于發生沖突。”(53)此一表述,道出了周氏分歧時期的某些思惟真實:五四漲潮后,其對儒家中庸的倡導與其趨于消極的現實姿態,體現出與道家隱逸思惟附近的一面;而在“七七事變”之后,周氏對釋聚會場地子“血性與胸襟”和儒家“事功”思惟的宣傳,則顯示了與道家隱逸思惟相沖突的另一面。
1937年7月,周作人借程明道用以批評孟子“蠻橫”的“英氣”一詞,指出孟子拒楊墨與韓愈辟佛都有掉儒家的不偏不倚(54)。但是,一年后,周氏則承認喜歡子路的兒子子崔向狐黡尋仇的故事,以為“軍人而有儒雅氣,殆是儒家幻想的傳說好漢”(55)。1940年頭,在《釋子與儒生》一文中,周氏引年夜慧禪師、貫休二位釋子愛君憂國的言行之后指出:“由是可知,釋子學佛,與墨者學禹,都不是不難事,非是有血性人不克不及到,若楊子為我,有如修小乘者,但了得四諦,至少多可獲阿羅漢果,終是自了漢,不成同日而語也。”之后,周氏筆鋒一轉:
據我們平常人想,儒家本是講實際的,并不是不重功利,那么其幻想當然是禹稷,孔子棲棲皇皇的奔忙,其來由無非是憂平易近,所以如是其急,比及沒法下手往干,這才來坐在樹下找幾個學生講講,所講的生怕還是 TC:9spacepos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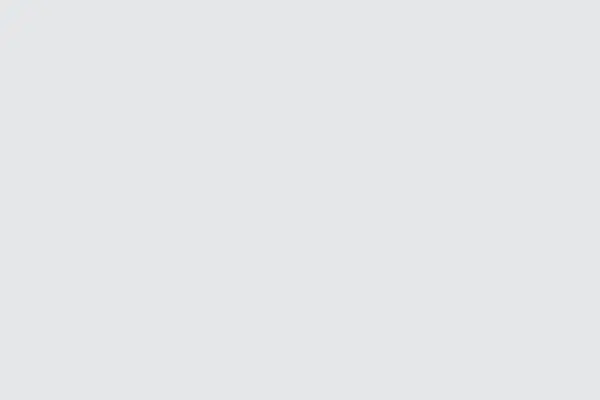
發佈留言